![êPé]](/common/images/pic_closed.pn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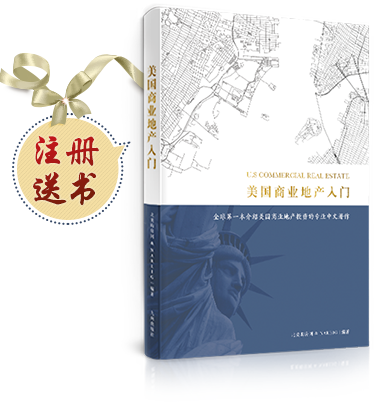
×¢ƒش²¢ح¨ك^ٍ×C¼´؟ة«@µأƒrضµ88شھ،¶أہ‡ّةجکIµط®aبëéT،·
زرسذظ~ج–£؟ ٌRةدµان› ½›¼oبث×¢ƒش
خززرé†×x²¢ح¬زâ،¶±±أہظڈ·؟¾Wسأ‘ôت¹سأ…f×h،·
خؤ»¯²»ئ½µب£؛أہ‡ّةْ»î·½ت½µؤث¥آنض®ش´
پيش´£؛http://finance.sina.com.cn/stock/usstock/c/20120126/043611259566.shtml×÷صك£؛±±أہظڈ·؟¾W

’كز»’ك£¬ëS•r؟´
أہ‡ّصشع·ضءرé_پي،£شعأہ‡ّڑvت·µؤ´َ¶à”µ•régہںoص“×ش£إc×îطڑ¸F‡ّأٌض®égµؤ²»ئ½µبذشسذ¶à¸ك£¬خز‚ƒ¶¼±£³ضضّتہ½çئنثûµط·½ثù›]سذµؤخؤ»¯ئ½؛â——ك@تاŒ¦°×بث¶ّرش،£
‚¥´َµؤأہ‡ّأٌض÷ضئ¶بؤê´ْس›¾ژصكپ†ڑvخ÷ث¹-µآ-حذ؟ث¾S –(Alexis de Tocqueville)شع19تہ¼o30ؤê´ْŒ‘µہ£؛“ش½تا¸»ش£µؤ‡ّأٌ¾حش½تا•·ا³£×¢زâت¹×ش¼؛²»أ“ëxبثب؛;دà·´µؤ£¬ثû‚ƒ½›³£¶¼•Œ’؛ٌµطŒ¦´ف^µحëAŒسµؤ‡ّأٌ£¬ƒAآ ثû‚ƒµؤدë·¨£¬أ؟جى¶¼إcثû‚ƒكMذذ½»ء÷،£”
أہ‡ّبث؛ـد²ڑgك@کس×شز•£¬µ«†–î}شعسع£¬ك@·Nصf·¨زر½›²»شظصوŒچ،£×ش20تہ¼o60ؤê´ْزرëxé_£¬ك@·NذإرِµؤصوŒچ¶بز»ض±¶¼شعuكMµطœpبُ،£
بث‚ƒصé_ت¼×¢زâµ½¾ق´َµؤّ™œد،£²èühشعصضخ¾«س¢ëAŒسضذ؟´µ½ءث¸ك°ءµؤ‘B¶ب£¬ك@‚€ëAŒسصJé×ش¼؛×î¾ك™àح£¬²¢أüءîأہ‡ّئنثûبث¶¼زھتـئن¼sتّ،£“ص¼îI”ك\„سµؤ؟¹×hصك‚ƒ„tشع½›ْ¾«س¢ëAŒسضذ؟´µ½ءثح¬کسµؤ–|خ÷£¬ك@‚€ëAŒسةْ»îشع؛ہص¬ضذ£¬³ث×ّث½بث‡ٹڑâ™C³ِذذ،£ثû‚ƒشع†–î}µؤز»‚€·½أوپيصf¶¼تاص´_µؤ£¬µ«ںoص“تاصضخ²»ئ½µبذشك€تا½›ْ²»ئ½µبذش£¬¶¼²»ؤـ·´س³ك@‚€†–î}µؤئص±é³ج¶ب،£خز‚ƒ¬FشعثùأوإRµؤتاز»‚€خؤ»¯²»ئ½µبµؤ†–î}،£
أہ‡ّبثك^ب¥³£³£•؟نز«“أہ‡ّةْ»î·½ت½”£¬ك@‚€¶جصZشع1960ؤêك€±»ئص±éت¹سأ£¬ؤا•rثû‚ƒثùصfµؤتاز»·N¹«أٌخؤ»¯£¬ك@·Nخؤ»¯Œ¢¸÷‚€ëAŒسµؤ½^´َ¶à”µأہ‡ّبث¶¼¸²ةwشعƒب،£ك@تاز»·N؛ةwبص³£ةْ»î½›ٍ·ضديµؤخؤ»¯£¬ز»·N؛ةw»éزِ،¢ص\ذإ،¢اعأم؛حٍ¯ص\µبأہ‡ّضذذؤƒrضµµؤ¹²ح¬س^ؤîشعƒبµؤخؤ»¯،£
شعك^ب¥50ؤê•régہك@·N¹«أٌخؤ»¯زر½›½âَw،£خز‚ƒ°lص¹³ِءثز»‚€ذآµؤةدŒسëA¼‰£¬ك@ز»ëAŒسضذµؤبث‚ƒ¶¼شّ½ستـك^¸كµب½جس£¬¶ّك@·N½جس½›³£¶¼تاشع¾«س¢ŒWذ£ضذ«@µأµؤ;ثû‚ƒسذضّح¬کسµؤئ·خ¶؛حگغ؛أ£¬ؤـŒ¢ئنإcض÷ء÷أہ‡ّبث…^·ضé_پي،£إc´ثح¬•r£¬خز‚ƒك€زر½›°lص¹جژءثز»‚€ذآµؤدآŒسëA¼‰£¬ئنجطص÷²¢·اطڑ¸F£¬¶ّتا³·ëxأہ‡ّ؛ثذؤخؤ»¯َwدµ،£
éءثصfأ÷ك@ƒة‚€ذآëAŒسض®égµؤ²î¾àسذ¶à´َ£¬×Œخزت×دبڈؤ¸üڈV·؛زâءxةدµؤةدضذ®aëA¼‰؛ح„ع„سëA¼‰ض®égµؤ·ض½ç¾€ضvئً£¬سأƒة‚€ج“ک‹µؤةç…^¼سزشêUلŒ£¬زشدآ·ض„e·Qé“طگ –أةجط”(Belmont)(شذحپي×شسع²¨ت؟îD¸½½üµؤز»‚€ةدضذ®aëA¼‰ةç…^)؛ح“Oو‚”(Fishtown)(شذحپي×شسعظM³اµؤز»‚€ةç…^£¬ك@‚€ةç…^×ش´َ¸ïأü•r´ْزشپيز»ض±¶¼تا°×بث„ع„سëA¼‰µؤ¾غ¾سµط)،£
¾حطگ –أةجط¶ّرش£¬خزڈؤب«أہ½yس‹”µ“ژىضذجلب،ظYءدµؤبث¶¼±طيڑضءةظ“يسذŒWت؟ŒWخ»£¬ئن¹¤×÷چڈخ»±طيڑتا½›ہي،¢لtژں،¢آةژں،¢¹¤³جژں،¢½¨ضژں،¢؟ئŒW¼ز،¢´َŒW½جتع»ٍأ½َwƒببفضئ×÷صك،£¾حOو‚¶ّرش£¬ثû‚ƒ±طيڑ“يسذ²»¸كسع¸كضذŒWڑvµؤŒWخ»;بç¹ûثû‚ƒسذ¹¤×÷£¬ؤاأ´±طيڑتاث{îI¹¤بث،¢تصمy†Tµب¼¼ذg؛¬ء؟ف^µحµؤ·„صکIچڈخ»،¢»ٍتاà]¾ضقkتآ†T»ٍ½س´†Tµب¼¼ذg؛¬ء؟ف^µحµؤ°×îIچڈخ»،£
·û؛دخزŒ¦طگ –أةجطض®زھاَµؤبث°ü؛¬´َ¼s20%µؤأہ‡ّ°×بث£¬ؤêgشع30ڑqµ½49ڑqض®ég;·û؛دخزŒ¦Oو‚زھاَµؤبث°ü؛¬´َ¼s30%µؤأہ‡ّ°×بث£¬ؤêgز²شع30ڑqµ½49ڑqض®ég،£
خزجط„eجô³ِµؤ°×بثتا·اہ¶،زلµؤ°×بث£¬ك@تاéءثêUأ÷أہ‡ّµؤخؤ»¯²î®گزر½›×ƒµأ¶àأ´ڈV·؛¶ّةîكh£¬زٍéخؤ»¯²»ئ½µبذش²¢·ازشبث·N»ٍ·N×هé»ùµA،£خزجط„eجô³ِ30ڑqµ½49ڑq——خز·Qض®éب«ت¢ؤêgëA¶خµؤ³ةؤêبث——تاéءث±يأ÷ك@ذ©ع…„ف²»ؤـزشكm»éؤêg»ٍحثذفؤêgپي×÷³ِ½âلŒ،£
شعطگ –أةجط؛حOو‚£¬ك@ہïثù°lةْµؤتآاé؟ةزشصfأ÷شع1960ؤêµ½2010ؤêض®égأہ‡ّµؤ¹²ح¬خؤ»¯°lةْءثت²أ´کسµؤ׃»¯،£
»éزِ£؛شع1960ؤ꣬ںoص“تاشعطگ –أةجطك€تاشعOو‚£¬½Y»éآت¶¼تادà®”ض®¸كµؤ£¬ا°صكé94%£¬؛َصكé84%،£µ½20تہ¼o70ؤê´ْ£¬ƒة‚€µط·½µؤ½Y»éآت¶¼سذثùدآ½µ£¬¶ّاز½µ·ù»ù±¾دàح¬،£µ«شظ´خزش؛َ£¬²î¾àé_ت¼×ƒ´َ،£شعطگ –أةجط£¬½Y»éآتشع20تہ¼o80ؤê´ْضذئع·€¶¨دآپي£¬µ½2010ؤêé83%;
µ«شعOو‚£¬½Y»éآتہ^ہmدآ½µ£¬½طضء2010ؤêƒHسذةظ”µبث½Y»é£¬ƒHé48%،£طگ –أةجطإcOو‚ض®égµؤ½Y»éآت²î¾àڈؤƒHƒH10‚€°ظ·ضücشِéLضء35‚€°ظ·ضüc،£
†خسH£؛»éزِµؤءيز»‚€·½أو——خ´»é‹Dإ®ةْ×سµؤ°ظ·ض±ب——ï@ت¾³ِح¬کس¾ق´َµؤ²î¾à،£ëmب»صضخ¼ز؛حضھأûأ½َw²»ش¸جلئً£¬µ«·ا»éةْس´_Œچتا‚€†–î}،£ںoص“°´ؤؤ·Nکثœتپي؛âء؟£¬خ´»é‹Dإ®µؤ×سإ®¶¼أوإRضّ±بëx»é·ٍ‹Dµؤ×سإ®²îµؤةْ»î£¬±بض®حêصû¼زح¥µؤ×سإ®„t¸üتا²îµأ¶à،£¼´ت¹تاشع؟¼‘]µ½¸¸ؤ¸µؤتصبë؛ح½جس†–î}زش؛َ£¬ك@·N²»تـڑgسµؤ¬FŒچز²بشإf´وشع،£
شع1960ؤ꣬ثùسذ°×بث³ِةْبث”µضذƒHسذ2%تا·ا»éةْµؤ،£®”خز‚ƒسع1970ؤêت×´خé_ت¼س›ن›ؤ¸سHµؤ½جسث®ئ½•r£¬شع½جس³ج¶ب²»³¬ك^¸كضذ(ز²¾حتا“يسذOو‚½جس³ج¶ب)µؤ°×بث‹Dإ®ضذ£¬·ا»éةْسµؤ×سإ®ثùص¼±بہé6%;¶ّµ½2008ؤêéض¹£¬سذ44%تا·ا»éةْµؤ،£شعطگ –أةجط“يسذ´َŒWŒWڑvµؤ‹Dإ®ضذ£¬½طضء2008ؤêéض¹سذ6%µؤ³ِةْبث”µتا·ا»éةْµؤ£¬آش¸كسع1970ؤê•rµؤ1%،£
اعأم¶ب£؛
شع1960ؤêزش؛َ£¬‹Dإ®¹¤×÷µؤکثœت°lةْءث¸ïأü»¯µؤ¸ؤ׃£¬µ«ؤذذشµؤ¹¤×÷کثœت„tت¼½Kبçز»£¬ؤا¾حتا·²تا½،؟µµؤؤذذش¶¼‘ھش“ب¥¹¤×÷،£µ«شعŒچëHةْ»îضذ£¬ك@·Nکثœتشعأ؟‚€µط·½¶¼تـµ½ءثاضخg،£شعOو‚£¬ك@·N׃„سسبئن„،ءز،£(éءث±ـأâ×î½üز»´خµؤ½›ْث¥حثŒ§ضآك@·N¬Fدَ±»»ىد£¬خزت¹سأءث½طضء2008ؤê3شآ·فéض¹µؤ”µ“پي×÷é؛âء؟ك@·Nع…„فµؤ½Küc)،£
شع„ع„سëA¼‰ضذ£¬اعأم¶بدآ½µµؤض÷زھض¸کثتا£¬ش½پيش½¶àµؤجژسع×î¼ر¹¤×÷ؤêgµ«ŒWڑv²»³¬ك^¸كضذµؤؤذذش·Qئنصز²»µ½¹¤×÷——ثû‚ƒزر½›“ضأةيسع„ع„سء¦بث؟عزشح┣¬ك@ز»°ظ·ض±بڈؤ1968ؤêµؤ3%µحücةدةضء2008ؤêµؤ12%،£12%µؤ”µ×ض؟´ئًپيثئ؛ُ›]ؤاأ´¶à£¬µ«ؤمذèزھ؟¼‘]µؤتا£¬خز‚ƒثùصfµؤتاؤاذ©ؤêgشع30ڑqµ½40ڑqض®égµؤؤذذش;¶ّ¸ù“ةٌت¥µؤأہ‡ّ‚÷½y£¬أ؟‚€أہ‡ّؤذذش¶¼‘ھ¹¤×÷»ٍصز¹¤×÷£¬¶ّ¬FشعسذŒ¢½ü°ث·ضض®ز»µؤبث›]سذك@کس×ِ،£إc´ثح¬•r£¬“يسذ´َŒWŒWڑvµؤؤذذش„t›]سذ°lةْج«¶à׃»¯£¬µ½2008ؤêƒHسذ3%²»شع„ع„سء¦بث؟عضذ،£
ءيز»‚€ضµµأ×¢زâµؤ¸ؤ׃تا£¬“²»×مب«آڑ¹¤×÷”µؤ±بآت°lةْءث¸ؤ׃،£شع“يسذ¹¤×÷µؤOو‚ؤذذشضذ£¬10%µؤبثشع1960ؤê•rµؤأ؟ضـ¹¤×÷•rég²»×م40ذ،•r£¬ك@ز»”µ×ضµ½2008ؤêةدةضء20%;¶ّشعطگ –أةجط£¬ك@ز»”µ×ضڈؤ1960ؤêµؤ9%ةدةضء12%،£
·¸×ïآت£؛·¸×ïآتµؤةدةت¼سع20تہ¼o60ؤê´ْضذئع£¬شع20تہ¼o80ؤê´ْضذہ^ہm°lص¹£¬ئنضذOو‚µؤ·¸×ïآت¼±„،ةدة£¬µ«طگ –أةجطژ×؛ُ›]سذ׃»¯،£ڈؤ1960ؤêµ½1995ؤ꣬Oو‚µؤ±©ء¦·¸×ïآتشِéLءثژ×؛ُخه±¶زشةد£¬¶ّطگ –أةجط„t»ù±¾³ضئ½،£×ش20تہ¼o90ؤê´ْضذئعزشپي£¬·¸×ïآتµؤدآ½µءîصû‚€‡ّ¼زتـزو£¬µ«Oو‚ثùتـس°ي‘ف^ذ،£¬ئن®”ا°·¸×ïآتبشدà®”سع1960ؤê•rµؤ4.7±¶،£
×ع½جذإرِ£؛ںoص“ؤم‚€بثµؤ×ع½جس^ؤîبç؛خ£¬¶¼ذèزھصJ×Rµ½´َ¼sسذز»°ëµؤأہ‡ّ´بةئتآکI،¢ض¾ش¸»î„س؛حةçˆF³ة†Tإc½ججأض±½سدàêP;ك€ذèزھصJ×Rµ½µؤتا£¬إcںo×ع½جذإرِµؤبثدà±ب£¬“يسذ×ع½جذإرِµؤأہ‡ّبثثùص¼سذµؤ·ا×ع½جةç•ظY±¾زھ¶àµأ¶à،£شعك@·Nh¾³دآ£¬×ش1960ؤêزشپيب«أہ·¶‡ْƒبµؤخؤ»¯زر½›×ƒµأ¸ü¼سںo×ع½ج»¯µؤذخ„فءîبث¸ذµ½²»°²;¶ّإcطگ –أةجطدà±ب£¬Oو‚µؤںo×ع½ج»¯ع…„ف¸ü¼س‡ہضط£¬ك@سبئنءîبث¸ذµ½²»°²،£ك@إcء÷ذذµؤس^ؤîدà·´£¬¼´إc„ع„سëA¼‰دà±ب£¬تہث×»¯µؤ¾«س¢بشإfˆش³ض×ع½جذإرِ;µ«پي×شسع¾C؛دص{²éي—ؤ؟(General Social Survey)µؤ×C“±يأ÷£¬ژ×؛ُ›]سذŒ¦ك@·Nع…„فجل³ِ®گ×hµؤسàµط،£
إeہپيصf£¬خز‚ƒŒ¢ؤاذ©ذû·Q×ش¼؛¸ù±¾›]سذ×ع½جذإرِ»ٍتاز»ؤêضذ×ِ¶Y°ف´خ”µ²»³¬ك^ز»´خµؤبث¶¨ءxé“ŒچëHةدµؤںo×ع½جصك”£¬ؤاأ´“1972ؤêµ½1976ؤêض®égµؤ¾C؛دص{²éي—ؤ؟ï@ت¾£¬29%µؤطگ –أةجطبث؛ح38%µؤOو‚بثڑwŒظسعك@ز»îگ„e;شعëS؛َµؤ30ؤê•régہطگ –أةجطبثµؤتہث×»¯±بہڈؤ29%ةدةضء40%(پي×شسع2006ؤêµ½2010ؤê¾C؛دص{²éي—ؤ؟µؤ”µ“)£¬¶ّOو‚بث„tڈؤ38%ةدةضء59%،£
؛ء²»؟نڈˆµؤصf£¬ك@·N·ضئçزرŒ¢طگ –أةجط؛حOو‚ضأسع²»ح¬µؤخؤ»¯h¾³دآ،£µ«تا£¬²»ƒHƒHتا„ع„سëA¼‰°lةْءث׃»¯£¬ةدضذ®aëA¼‰ز²زر½›±³ëxءث×ش¼؛µؤ‚÷½y،£
بç¹ûؤمتا1960ؤêةْ»îشعطگ –أةجطµؤز»أû¹«ث¾¸ك¹ـ£¬ؤاأ´تصبë²»ئ½µبذشŒ¢°رؤمإcةْ»îشعOو‚µؤ½¨ض¹¤بث…^·ضé_پي£¬µ«شعخؤ»¯ةد„tژ×؛ُ²»´وشع؛ـ´َµؤ²»ئ½µبذش،£ؤمك^ضّ¸»ش£µؤةْ»î£¬µ«²¢·ات®·ضإc±ٹ²»ح¬µؤةْ»î،£ؤمµؤڈN·؟¸ü´َ£¬µ«ؤم²»•سأثüپي×ِثلؤجہز؛حؤ½ث¹ہï×ِشç²ح;ؤمµؤëٹز•™Cئءؤ»¸ü´َ£¬µ«ؤم؛ح½¨ض¹¤بث¶¼؟´شS¶àح¬کسµؤ¹ؤ؟(زٍéؤم›]سذج«¶àكx“ٌ);ؤمµؤ·؟×سہï؟ةؤـ“يسذز»‚€½¨ض¹¤بث·؟×سہï›]سذµؤث½بثذ،·؟ég£¬µ«ك@‚€·؟égہï²»•سذStairMaster»ٍذ،ذح½،ةيسخس¾³ط(Lap Pool)µب½،ةيشOت©£¬ز²²»•سذبخ؛خسأپي±O؟طؤمَwض¬·¾µؤƒxئ÷،£ؤم؛ح½¨ض¹¤بث¶¼•؛بBud،¢Miller،¢Schlitz»ٍPabs£¬µ«ؤم²»•؛ب“¾«ئ·ئ،¾ئ”(boutique beer)،£ؤم؛ح½¨ض¹¤بث؛ـ؟ةؤـ¶¼•³éںں;µ«بç¹ûؤم²»³éµؤش’£¬ؤاأ´²»•شع„eبث³éںںµؤ•r؛ٍفpأïµطµةضّثû‚ƒ،£
شع¶ب¼ظ•r£¬ؤم؛ح½¨ض¹¤بث؛ـ؟ةؤـ¶¼•ژ§ضّ¼زبثب¥؛£ك…»ٍتاب¥×ِلô~؛½ذذ£¬µ«ؤم‚ƒ¶¼²»•×،خهذا¼‰¾ئµê،£بç¹ûؤمشّµ½أہ‡ّ¾³حâآأسخ(؛ـ؟ةؤـؤمڈؤخ´ب¥ك^)£¬ؤاأ´•تاب¥ڑWضقµؤز»´خذشآأذذ£¬شع14جى•régہïسخس[8‚€³اتذ£¬¶ّ²»تا¬Fشعأ؟ؤ궼•سذµؤƒةب´خ¾³حâسخضذµؤز»´خ£¬ك@ذ©آأذذسذ؟ةؤـتاةج„صآأذذ،¢…¢¼س•×h»ٍتاشع¸çث¹ك_ہè¼سµؤشئىFءضضذ¶بك^µؤةْ‘B¼ظئع،£
ؤم‚ƒ؟ةؤـ¶¼×،شع´َ¶à”µبثض»سذ¸كضذŒWڑvµؤ½ض…^ضذ£¬؟ةؤـؤم×ش¼؛ز²تائنضذز»†T،£ؤمضـ‡ْµؤبثضذبç¹ûسذبث“يسذ´َŒWŒWخ»£¬ؤاأ´ژ×؛ُز»¶¨تاڈؤضفء¢´َŒW»ٍذ،ذح½ج•ŒWش؛ضذ«@µأءثك@·NŒWخ»£¬ك@ذ©ŒWذ£ضذµؤŒWةْ´َ¶à”µ¶¼تا¼زح¥ضذµعز»´ْةد´َŒWµؤبث،£³·اتاشعŒWذg½ç،¢ح¶ظYمyذذ،¢ةظ”µ»ù½ً،¢ضذرëاéˆَ¾ض(CIA) ؛ح‡ّ„صش؛ضذ¹©آڑ£¬·ٌ„tؤم؛ـ؟ةؤـ²»تا®…کIسع¹·ً،¢ئصءضث¹îD»ٍتاز®ô”،£
¼´ت¹تاŒ¢ؤمإc½¨ض¹¤بث…^·ضé_پيµؤتصبë²»ئ½µبذش£¬ز²؛ـ؟ةؤـتاشعؤم³ةؤêزش؛َ²إ³ِ¬Fµؤ،£ؤمµؤ¸¸ؤ¸؛ـ؟ةؤـز²تا„ع„سëA¼‰»ٍضذ®aëA¼‰£¬ثû‚ƒµؤتصبëإc½¨ض¹¤بث›]سذج«´َ²»ح¬£¬ثû‚ƒز²شّ¾س×،شعإc½¨ض¹¤بث؛ـدàثئµؤةç…^ضذ£¬ؤمڈؤح¯ؤêئً¾حتىد¤ءث½¨ض¹¤بثµؤةْ»î½Yک‹،£
ءيحâذèزھض¸³ِµؤتا£¬¬FشعŒ¢طگ –أةجطبثإcOو‚بث…^·ضé_پيµؤ²î®گ²¢·اؤëyذشµؤ£¬µ«خزجلµ½ك^µؤةدضذ®aëA¼‰µؤح»ب»قD׃——ثلؤجہز؛حؤ½ث¹ہïµبضTبç´ثîگ——تاز»·Nشعطگ –أةجط°lص¹ئًپيµؤ…^·ضذش»î„س،£ك@إcطگ –أةجطبثثù³شµؤت³خï،¢ثû‚ƒµؤï‹ت³ء•‘T،¢ثû‚ƒ½Y»éةْ×سµؤؤêg،¢ثû‚ƒé†×xµؤ•ّ¼®(¼°ئن”µء؟)،¢ثû‚ƒثù؟´µؤëٹز•„،؛حëٹس°(زش¼°»¨شع؟´ëٹز•؛حëٹس°ةدµؤ•rég)،¢ثû‚ƒد²ڑgµؤسؤؤ¬·½ت½،¢ثû‚ƒصصءد×ش¼؛ةيَwµؤ·½ت½،¢ثû‚ƒ·؟×سµؤرbï—·½ت½،¢ثû‚ƒµؤذفée»î„س،¢ثû‚ƒµؤ¹¤×÷h¾³،¢زش¼°ثû‚ƒًBس؛¢×سµؤ»î„سسذêP،£؟‚َwپيصf£¬ك@ذ©¶¼تاخؤ»¯ةدµؤ²î®گذش،£
ك@·Nاé›rصشع׃µأ¸ü¼سشم¸â،£طگ –أةجطبثضذµؤز»‚€ذ،ˆFَw°üہ¨ؤاذ©زر½›كMبëأہ‡ّةدŒسة畵ؤبث£¬ثû‚ƒ¹ـہيضّصû‚€‡ّ¼ز£¬ك@زâخ¶ضّثû‚ƒ•éؤمؤـ؟´µ½ت²أ´ëٹس°؛حëٹز•„،ط“طں£¬éؤمؤـ؟´µ½؛ح×xµ½ت²أ´ذآآ„ط“طں£¬éأہ‡ّ¹«ث¾؛ح½ًبع™Cک‹µؤأüك\ط“طں،¢éص¸®„“شىµؤ·¨آةَwدµ؛ح·¨ءî·¨زژط“طں،£ثû‚ƒتاذآإdµؤةدŒسëA¼‰£¬إcطگ –أةجطبثدà±ب£¬ثû‚ƒإcأہ‡ّئصح¨´َ±ٹةْ»îض®égµؤ²î¾à¸ü´َ——ك@·N²î¾à²»ƒHتاةç•ذشµؤ£¬ح¬•rك€تا؟صégذشµؤ،£ك@·N¾«س¢ëAŒسµؤ³ة†Tصبصزو°´صصà]ص¾ژ´aŒ¢ئن×شةي¼ڑ·ض铳¬¼‰¸»سذ”؛ح“³¬¼‰¾«س¢”ƒة·N£¬زٍ´ثخزŒ¢ئن·Q铳¬¼‰à]¾ژ”(SuperZIP)،£
شع1960ؤ꣬أہ‡ّزر½›زشضّأû¾«س¢ةç…^µؤ·½ت½“يسذدà®”سع“³¬¼‰à]¾ژ”µؤبثب؛——بç¼~¼sµؤةد–|…^،¢ظM³اµؤMain Line،¢ض¥¼س¸çµؤNorth Shore؛ح±ب·ًہûة½اf(Beverly Hills)µب،£µ«تا£¬ëmب»ك@ذ©¾«س¢ëAŒس“يسذآ•حû£¬µ«ك@ز»ëAŒسضذµؤبث²¢²»ز»¶¨´َ¸»´َظF£¬ةُضءخ´±طةْ»î¸»ش£،£شع1960ؤê×îضّأûµؤ¾«س¢ةç…^ضذ£¬سذ14‚€ةç…^µؤ¼زح¥ئ½¾ùتصبëص„²»ةد¸»ش££¬ƒHé8.4بfأہشھ(°´½ٌجىµؤظڈظIء¦س‹ثم)،£شعك@ذ©¾«س¢ةç…^ضذ£¬ƒHسذثؤ·ضض®ز»µؤ³ةؤêبث“يسذ´َŒWŒWڑv،£
µ½2000ؤê•r£¬ك@·N²î®گسذثù؟sص£¬ةدتِ14‚€¾«س¢ةç…^ضذµؤ¼زح¥ئ½¾ùتصبë·ءثز»·¬£¬ضء16.3بfأہشھ;“يسذŒWت؟ŒWخ»µؤ³ةؤêبثµؤ±بہé67%£¬كh¸كسع1960ؤê•rµؤ26%،£¾«س¢ةç…^²»ƒHص׃µأح¬کس¸»سذ؛ح“يسذف^¸كµؤ½جس³ج¶ب£¬ح¬•rك€شعذخ³ةش½پيش½¶àµؤب؛½M،£
بç¹ûؤم±»رûصˆ…¢¼سز»أûبAت¢îD¾«س¢µؤرç•£¬ؤاأ´ؤم؛ـ؟ةؤـŒ¢پيµ½ئنخ»سع†جضخ¶طµؤ¼زضذ،£†جضخ¶طشظ¼سةدخ÷±±جط…^(Northwest D.C،£)،¢Chevy Chase،¢طگبûث¹ك_(Bethesda)،¢²¨¶àٌR؟ث(Potomac)»ٍûœ؟ثبR¶÷(McLean)£¬ك@ذ©µط…^؟‚¹²°ü؛¬ءث13‚€دààڈµؤà]ص¾ژ´a،£بç¹ûت¹سأز»‚€»ùسع½جس؛حتصبëµؤض¸”µپيŒ¦صû‚€أہ‡ّµؤثùسذà]ص¾ژ´aكMذذإإءذ£¬²¢Œ¢ئن°´°ظ·ضخ»كMذذ·ض½M£¬ؤاأ´Œ¢•°l¬Fك@13‚€à]ص¾ژ´aضذسذ11‚€جژسعµع99‚€°ظ·ضخ»ةد£¬ئنثûƒة‚€جژسعµع98‚€°ظ·ضخ»ةد،£سذ10‚€à]ص¾ژ´aجژشعµع99‚€°ظ·ضخ»µؤةد°ë²؟·ض،£
شع¼~¼sتذ،¢آهة¼´‰،¢إf½ًة½-ت¥؛خبûµط…^،¢²¨ت؟îD¼°ئنثûز»ذ©´َ³اتذµط…^£¬ز²؟ةزشصزµ½دàثئµؤ“³¬¼‰à]¾ژ”ب؛½M،£سةسعشعك@‚€‡ّ¼زضذك\ I´َذح¹«ث¾ح¨³£¶¼زâخ¶ضّةْ»îشعك@ذ©³اتذضذµؤز»‚€¸½½ü£¬سة´ث؟ةزشµأ³ِµؤ½Yص“تا£¬إc1960ؤê•rµؤ¾«س¢ëAŒسدà±ب£¬®”ا°أہ‡ّµؤ¾«س¢ëAŒسŒچëHةدةْ»îشعز»‚€خؤ»¯كhéد،±،؛ح¹آء¢µؤتہ½çضذ،£
ك@·N¹آء¢¬Fدَك€شع׃µأ¸ü¼سگ؛»¯£¬¹ـہيك@‚€‡ّ¼زµؤبث‚ƒصش½پيش½¶àµطشعك@‚€تہ½çضذصQةْ،£إc1960ؤê•rµنذحµؤ¾«س¢ëAŒس³ة†T²»ح¬£¬ثû‚ƒŒ¦ذآµؤةدŒسëA¼‰خؤ»¯زشحâµؤئنثûخؤ»¯ز»ںoثùضھ،£خز‚ƒصشع؟´µ½ش½پيش½¶àµؤ¾«س¢ëAŒسµعب´ْ³ة†T£¬ثû‚ƒµؤ×و¸¸ؤ¸ةُضء¶¼²»ؤـ½oئنژ§پيز»‚€ءث½âئنثûأہ‡ّبثةْ»îµؤ´°؟ع،£
ك@ذ©ذآµؤةدŒسëA¼‰؛حدآŒسëA¼‰é؛خ•®aةْؤط?شعصfأ÷ذآµؤدآŒسëA¼‰ذخ³ةµؤ†–î}ةد£¬ڈؤ×َزيس^üc³ِ°lµؤ؛††خشڈلŒتاص¾²»×،ؤ_µؤ£¬ئنشزٍ²¢·اشعسع°×بث„ع„سëA¼‰ضذµؤؤذذش²»شظؤـ‰ٍظچب،ت¹ئن؟ةزش½Y»éµؤ“¼زح¥¹¤ظY”£¬زٍéشع2010ؤêضذ£¬„ع„سëA¼‰¹¤×÷چڈخ»ةدµؤز»°مؤذذش¹¤×÷صكµؤتصبëإc1960ؤêتادàح¬µؤ;ز²²¢·اشعسعگ؛ءسµؤ¾حکIتذˆِŒ§ضآذؤ»ززâ‘ذµؤؤذذش¹¤×÷صكحث³ِ„ع„سء¦بث؟ع£¬زٍéشع²»؛أµؤؤê¾°ضذ£¬حث³ِ„ع„سء¦بث؟عµؤبث”µشِéLثظ¶بإc20تہ¼o80ؤê´ْ؛ح90ؤê´ْزش¼°21تہ¼o00ؤê´ْµؤ½›ْ·±کs•rئعضذتادàح¬µؤ،£
صبçخزشع´ثا°µؤ´َ¶à”µخؤصآضذثùض¸³ِµؤؤاکس£¬خزصJé20تہ¼o60ؤê´ْضذµؤ¸ؤ¸ï»î„ستااé›rگ؛»¯µؤé_¶ث،£شعك@‚€ؤê´ْضذ£¬Œ¦إ®ذش¶ّرش£¬ةç•ص²كµؤ¸ؤ׃ت¹ئنشع›]سذصة·ٍµؤاé›rدآةْس×سإ®شع½›ْةد׃µأ¸ü¼س؟ةذذ;Œ¦ؤذذش¶ّرش£¬ك@·N¸ؤ׃ت¹ئنؤـشع›]سذ¹¤×÷µؤاé›rدآك^»î،£ةç•ص²كµؤ¸ؤ׃ك€ت¹µأبث‚ƒؤـڈؤتآ·¸×ï»î„س¶ّںoذè³ذ“ْ؛َ¹û;Œ¦سعجژہيثùشعةç…^ضذµؤ†–î}پيصf£¬ش±¾±طيڑسةؤم؛حàڈ¾سجژہيµؤ†–î}؟ةزشسةص¸®پي¸ü¼سبفز×µط¼سزش½â›Q،£
²»ك^£¬ڈؤŒچسأذش½ا¶بپيضv£¬ہي½âذآµؤدآŒسëA¼‰é؛خذخ³ة²¢·اجط„eضطزھ،£ز»µ©ذخ„فé_ت¼گ؛»¯£¬ؤاأ´ز»‚€×شخز¼سڈٹµؤرh¾ح•ةْ¸ù£¬شزٍتا‚÷½yةدڈٹ´َµؤةç•زژ·¶زرحء±ہحك½â،£سةسعك@ز»ك^³جزر׃µأ¾كسذ×شخز¼سڈٹذشµؤ¾‰¹ت£¬ؤؤإآتاڈU³20تہ¼o60ؤê´ْ•rµؤ¸ؤ¸ï´ëت©(ك@·Nتآاéتا²»•°lةْµؤ)£¬ؤاأ´ڈؤ×î؛أµؤ³ج¶بةدپيصf£¬ز²ض»ؤـتا¾ڈآµط¸ؤ׃ك@·Nع…„ف،£
إc´ثح¬•r£¬´ظت¹ذآµؤةدŒسëA¼‰ذخ³ةµؤحئ„سء¦„t²¢·ابخ؛خبثµؤهeص`£¬¶ّازك@ذ©حئ„سء¦¾كسذµضسù²ظ؟vµؤجطذش،£ںoص“بç؛خ£¬تذˆِî^ؤXµؤ½›ْƒrضµ¶¼Œ¢ہ^ہmشِéL;ںoص“بç؛خ£¬أ؟ز»´ْبثضذ×î³ة¹¦µؤبثت؟¶¼Œ¢ƒAدٍسع»¥دà½Yé·ٍئق،£سذ»ùسع´ث£¬×î³ة¹¦µؤأہ‡ّبثŒ¢ہ^ہm³¯ضّ×÷éز»‚€ëA¼‰¶ّى–¹ج؛ح¹آء¢µؤ·½دٍ°lص¹دآب¥،£¸»ش£بثب؛ك…ëH¶گآتµؤ׃„س²»•ءîك@·Nع…„فسذثù¸ؤ׃£¬„ع„سëA¼‰×سإ®ھ„ŒW½ًµؤجل¸كز²²»•ءîئنسذثù¸ؤ׃،£
خ¨ز»ؤـ¸ؤ׃ك@·Nع…„فµؤتا£¬ثùسذëAŒسµؤأہ‡ّبث¶¼صJ×Rµ½´وشعخؤ»¯²»ئ½µبذشك@‚€†–î}£¬²¢صJ×Rµ½±طيڑ×ِذ©ت²أ´پي½â›Qك@‚€†–î}،£ك@ہïثùصfµؤ“×ِذ©ت²أ´”إcص¸®حئ³ِذآµؤس‹„»ٍ·¨زژںoêP،£¹«¹²ص²ك®”ب»•Œ¦خؤ»¯شى³ةس°ي‘£¬µ«²»ذزµؤتا£¬ںoص“تا±£تطµؤة畹¤³جك€تا×شسة»¯µؤة畹¤³ج£¬¶¼•ژ§پيح¬کس؟ةإآµؤس‹„حâ؛َ¹û،£
خزذؤضذثùدëµؤ“×ِذ©تآا锣¬±طيڑڈؤأہ‡ّ¼زح¥‚€َwزش×شةيہûزو¼°ئن×سإ®ہûزوéزہڑwپي²ةب،ذذ„سك@ز»·½أو×÷³ِ¶¨ءx£¬¶ّزھشعOو‚ك@کس×ِ¾ح±طيڑ«@µأپي×شسعحâ²؟µؤض§³ض،£¹«±ٹأہµآ؛حأہ‡ّ„ع„سëA¼‰µؤ…¢إcبشإfتا½â›Q†–î}µؤ؛ثذؤ£¬ا°جلتاؤاذ©ش‡ˆD×ِص´_µؤتآاéµؤبث‚ƒؤـ«@µأثû‚ƒثùذèµؤض§ش®——²¢·ازشص¸®·ِ³ضµؤذخت½£¬¶ّتاثû‚ƒہ^ہmˆش³ضµؤƒrضµ؛حکثœتµأµ½؟د¶¨،£ذآµؤةدŒسëA¼‰ثùؤـ²ةب،µؤ×î؛أµؤض§ش®´ëت©¾حتا·إ—‰ئن¸»سذƒش½¸ذµؤ“إذ”àب±·¦ض÷ءx”(nonjudgmentalism)،£Œ¦سعزر»éµؤ،¢تـك^½جسµؤبث‚ƒپيصf£¬بç¹ûثû‚ƒاعاع‘©‘©µط¹¤×÷£¬ہدہدŒچŒچµطًBس×سإ®£¬ؤاأ´¾ح‘ھ؛ء²»ھqش¥µط·´Œ¦ؤاذ©أïز•ك@ذ©œت„tµؤبث،£شع»éزِ؛حآڑکIµہµآµؤ†–î}ةد£¬ذآµؤةدŒسëA¼‰±طيڑé_ت¼زش×شةيéہپيكMذذ²¼µہ،£
“³¬¼‰à]¾ژ”ةْ»îµؤ׃»¯زھاَذآµؤةدŒسëA¼‰³ة†Tضطذآ؟¼‘]×ش¼؛ذèزھƒدبب¥×ِµؤتآاé،£ك@ہïسذز»ذ©جل×h؟ةؤـ•Œ¦ئنئًµ½ض¸Œ§×÷سأ£؛إcبخ؛خبث¸ô½^é_پيµؤë[¾سةْ»î²¢خ´زâخ¶ضّؤم×ش¼؛زھƒAدٍسع×شخزدقضئ;ؤم¾س×،µط¸½½üµؤبث‚ƒ›]سذت²أ´†–î}ذèزھ؛د×÷»¯µؤ½â›Q·½°¸£¬ك@·Nاé›rƒAدٍسعتا؟فشï·¦خ¶µؤ;شعذآµؤةدŒسëA¼‰“ïwµط”زشح⣬أہ‡ّµؤئنثûµط·½بشإfأہأµ½جژ¶¼تاآ”أô،¢سذب¤؛حءîبثسنگ‚µؤبث‚ƒ،£بç¹ûؤم²»تاك@کسµؤأہ‡ّµؤز»·ف×س£¬ؤاأ´ؤم¾حتا×شخز„ƒٹZءثءîأہ‡ّبث׃µأجط„eµؤ´َ¶à”µ–|خ÷،£
ك@·Nƒدب؟¼‘]µؤتآي—¶¼ؤـشعشS¶àîگثئµؤ›Q¶¨ضذµأµ½َw¬F£؛ؤمŒ¢شعؤؤ‚€ةç…^ظڈظIدآز»´±·؟خف£¬ؤمŒ¢é×سإ®كx“ٌµؤدآز»‚€ŒWذ££¬ؤمŒ¢Œ¦×سإ®بç؛خêUتَِwء¦„ع„س؛ح±ّزغµؤƒrضµ؛حأہµآ£¬ؤمتا·ٌ•·eکOµط…¢¼س×ع½ج¼¯•(زش¼°ؤمكx“ٌؤؤ·N¼¯•)زش¼°ؤمتا·ٌ•¸ü¶àµط…¢إcةç…^ةْ»î¶ّ·ا´بةئ»î„سµب،£
شعذآµؤةدŒسëA¼‰ضذ£¬أ؟‚€بث¶¼“يسذ×م‰ٍµؤط”„صظYش´پي×÷³ِز»دµءذµؤڈV·؛›Q¶¨£¬ك@ذ©›Q¶¨Œ¢تاز»·N›Q¶¨ذشµؤزٍثط£¬Œ¢إذ¶¨ثû‚ƒتاŒ¢×شةي¼°ئن×سإ®ح¶بëµ½ئنثûأہ‡ّبثضذب¥£¬ك€تاكx“ٌ×شخز¹آء¢،£خ¨ز»µؤ†–î}¾حتا£¬ثû‚ƒ¸üد²ڑgؤؤ·Nكx“ٌؤط،£
ك@کس¾ححêءث†ل?›]سذت²أ´جل¾VêüîIµؤس‹„?ëyµہخز‚ƒزھدàذإشSشS¶à¶àµؤ¸¸ؤ¸Œ¢•×ش°lµط،¢ض÷„سµطéثû‚ƒ×ش¼؛¼°ئن×سإ®×ِ³ِص´_µؤكx“ٌ£¬ڈؤ¶ّéك@‚€‡ّ¼ز×ِ³ِص´_µؤكx“ٌ?
تاµؤ£¬خز‚ƒض»ؤـك@کسدàذإ£¬µ«خز²»صJéك@تاجىصوµؤدë·¨،£خززر½›؟´µ½ءثشS¶àµؤغEدَ£¬±يأ÷خزثùأèتِµؤع…„فزر½›ءîشS¶àبث¸ذµ½“ْ‘n،£
بç¹ûسذ×م‰ٍµؤأہ‡ّبثؤـح¸ز•ك@‚€†–î}µؤ±¾ظ|£¬ؤاأ´ثû‚ƒ¾حŒ¢ذقڈحك@‚€†–î}،£ز»‚€¼زح¥ز»‚€¼زح¥µؤپي£¬éءثثû‚ƒ×ش¼؛µؤہûزو،£ك@¾حتاأہ‡ّبثµؤµہآ·،£
±¾¾W×¢أ÷،°پيش´£؛±±أہظڈ·؟¾W،±µؤثùسذ×÷ئ·£¬°و™à¾ùŒظسع±±أہظڈ·؟¾W£¬خ´½›±¾¾Wتع™à²»µأقDفd،¢صھ¾ژ»ٍہûسأئنثü·½ت½ت¹سأةدتِ×÷ئ·،£ك`·´ةدتِآ•أ÷صك£¬±¾¾WŒ¢×·¾؟ئندàêP·¨آةطںبخ،£ ·²±¾¾W×¢أ÷،°پيش´£؛XXX£¨·ا±±أہظڈ·؟¾W£©،±µؤ×÷ئ·£¬¾ùقDفd×شئنثüأ½َw£¬قDفdؤ؟µؤشعسع‚÷كf¸ü¶àذإد¢£¬²¢²»´ْ±ي±¾¾Wظح¬ئنس^üc؛حŒ¦ئنصوŒچذشط“طں،£
کث؛£؛أہ‡ّةْ»î
ةدز»ئھ£؛أہ‡ّةْ»î³ة±¾´َص{²é َwٍةد°à×هµؤز»جى... دآز»ئھ£؛،¾¼{إءدµءذءù،؟£؛Realm¾ئاfµؤ‚÷ئو...
